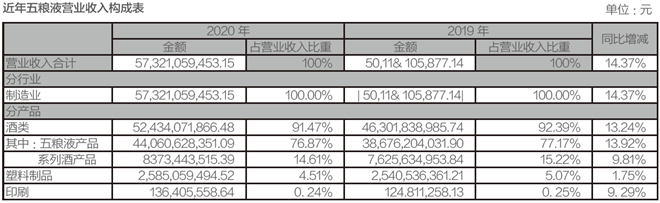沉浸成为人与城市、人与文化、文化与城市共存的主要形态。人成为文化与城市的主要感知主体,而文化成为连结人与城市的主要纽带,城市则是承载人与文化的容器。
文/ 刘祥(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旅游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著名城市文化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中文译作《城市文化》版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是城市的生命”。文化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天时、地利、人和,成都无疑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令人惊喜之处。在天时上,成都发挥鸭子浮水精神,GDP 已经进入全国城市前列,城市形象的品牌传播做得有声有色,Panda City 早已声名远播。在地利上,成都已经成为中国中西部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中心城市,是拉动中西部经济增长点的重要火车头,在城乡融合、文化传播发展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亮点。在人和方面,安逸不仅仅限于成都人的口头禅,而是成为新时代成都兼容并蓄、开放融合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成都如同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播的万花筒。
城市文化传播的基本命题
如何将文化与传播进行结合?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传什么与怎么传。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方法。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内容进行传播是首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选取内容的特点决定了如何进行传播。在硬件上,成都富有历史遗迹、人文名胜与城市建设等,视觉冲击力强,比较直观。从软件上,成都在公众认知中往往与“休闲”联系在一起,而“休闲”这个词在成都方言中就是“安逸”,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成都的城市气质,也是成都在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定位,更是成都市民日常的生活状态与思维特点。
从方法的角度看,传播是城市文化对外释放与沟通的主要渠道,随着人类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传播方式。在这些变幻的传播方式中,人是永远的主体,技术与工具则由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以成都为例,古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千古流传,不仅为成都留下了杜甫草堂这样的城市文化地标,更使得“诗意成都”有了来自历史的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宽窄巷子不仅仅是一种历经漫长岁月洗礼的珍贵历史遗留之物,更是流传千古的杜甫名句的绝佳视觉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软性的符号可能比硬性的符号更能够经住岁月的洗礼,而软性文化符号构成了城市文化传播中的软实力。
城市,巨大的文化感官
当下,城市与文化的关系有了新可能。
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我们身处在一个符号时代,每个人都被各种符号包围,人的社会位置也被用符号加以衡量。人类对符号的接触需要通过自己的感官来实现,所以感官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要突出。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感官,人们通过城市这个感官来去感知整体的外界环境,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城市这个巨大的感官之中。
人们通过城市中丰富的媒介信息来了解天气、交通出行与职场招聘等信息,企业通过城市对经济与生产要素的集聚功能,以及对产业链条的吸附能力来对接客户、遴选供应商与寻找新的增长点。离开了城市,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企业的商业经营与活动也陷于瘫痪,市场资源、生活要素与信息资讯都高度依赖城市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官。
城市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官,更是无数个这种个体感觉的抽象化,换言之,城市自己也形成了一个感官现实,就像一个巨大的场域,包含了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人和组织。
人们日夜处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感官之中,就像身处一个巨大的迷城,自身的行为、思想与观念正在被默默地重塑与建构,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不能理解与接受没有水电的日子,也无法面对周末没有餐馆、电影院与购物中心的状况。
城市容纳了数不清的个体感官,这些个体感官又通过城市的组织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官系统,城市成为这个巨大感官系统的承载体,个体感官通过城市感官感知外部环境与世界。城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文化感官。
城市文化传播的新革命——沉浸式共存沉浸成为人与城市、人与文化、文化与城市共存的主要形态,在这个沉浸状态中,人、文化与城市三者的边界在逐步消弭,人成为文化与城市的感知主体,而文化成为连结人与城市的主要纽带,城市则是承载人与文化的容器。
既然沉浸成为当代城市与文化的主要存在方式,那么我们看待城市、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时不可能忽视这一重要特征,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沉浸”这个概念。“沉浸”包含两个方面——体验与场景。
体验主要是指我们在与客观事物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感受与认知,好的体验会带来愉悦,恶劣的服务带来的体验感就会很差,在向别人诉说时会强化这一点。在互联网经济发达的今天,用户的体验对于一个商业机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绩效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体验在人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中也同样成立。
通过体验,人们可以感知城市与文化的存在;通过体验,人们去触摸城市发展与文化迭代的脉搏。南京夫子庙中的科举博物馆通过设置九曲回转的书简长廊,让参观的公众在刚步入时就能够感受到存续千年的中国文脉的强烈冲击,在刻意设计的长廊中感受科举的漫长历史与每一个参与个体的艰辛,参观者也因此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印象深刻,对南京夫子庙乃至南京作为“东南文都”的心理认知会更加强烈,这就是典型的通过用户体验设计增强城市文化传播效果的案例。
要做到真正的沉浸,除了关注体验这个环节外,还需要注意到场景。场景这个词本来是用于影视表演领域,在互联网时代被借用指代特定的时空维度下人与物的关系,通俗地讲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会做什么。
场景不但可以量化管理人的体验,更可以激发、引导、增强人的体验感。如今遍布各个城市的超级购物中心,通过巨大的体量营造了一个无所不备的巨型消费场景,人在这个场景中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即时性服务和产品,包含了餐饮、娱乐、购物等多种消费形态,这种巨大的、封闭的物理空间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舒适、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360 度环绕的消费场景之外,更激发了人的消费欲望、提升了人的消费体验,在这个巨大的消费场景中人的体验感会被无限拉伸,对于时空的敏感度会被降低,很多人可以在其中消磨一天而浑然不觉。
如果把这种超级购物中心放大,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场景。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场景中,文化可以是一个个具体的体验点位,也可以是由点到面的体验流程,更可以成为囊括消费、教育、出版等多种业态的综合体验场。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场景中,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全域、全要素、全维度的特征,文化的体验可以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空间点上,比如城市商圈、绿道及交通工具上,也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与城市相关的刷屏事件。
城市文化的沉浸式场景必然给人们带来全场景、全体验与全感官的冲击,人们浸润在城市文化中,身处城市的地理空间内,行为更加追求体验价值感,同时与城市这个场景的结合程度日趋紧密。
成都的存在意义
将城市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体验空间,从沉浸入手去建构城市文化传播的范式,此种思路在以往的中国城市文化传播实践中是稀缺的,但并不是说每个城市都具备这样的操作条件与基础。文化与城市的共存状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某些地方,城市与文化是撕裂与对立的,有些则是扭曲与脱离的。
放眼全国,成都无疑具备了这一潜质,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的文化,成都的城市文化是一种人文浸润式文化,像一滴滴雨露一样浸入这个城市每一片砖瓦与墙壁的缝隙之间,浸入了每一个成都市民的毛细血管之中,浸入了成都的每个社区、文化街道与城乡融合之中,成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物质文化形态,历史的与现代的,新城与老城;也有虚拟文化形态,成都人的安逸与开拓,诗意与享受,成都不仅完整保留了自身的文化基因,也在无意间契合了当下互联网时代体验至上的发展趋势。
城市文化的传播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需要顶层设计与来自上层的强力推动,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与阶层中的文化碎片整合起来,把分布在历史长河与现代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抽象出来,从而形成有关城市的文化主脉。欣喜的是我们在成都看到并深刻体会到了主政者在城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与作用。
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天府文化”作为对成都城市文化的引领性概念,这一抽象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一种超前的意识,即把天府文化的塑造和传播视为城市战略的重要部分,通过文化的亲和力与渗透力来关联城市内外的人群,通过文化的连结性实现对城市各要素的整合,以文化传播城市,以文化承载城市,以文化滋养城市。成都,无疑将在以上方面给我们带来期望与可能。
以往我们提到文化的传播,容易犯两个毛病,一个是虚无主义,一个是狭隘主义。
成都的城市文化并没有浮在表面,而是浸入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与每个人身上,对于成都城市文化的解读也绝不仅仅限于川戏、川菜等,乡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所进行的文创产业赋能,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城乡融合与文化传播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城市绿道与文化长廊的共生共融也使得我们明白文化其实可以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社区咖啡馆的公益运营也探索出了一条社区服务与文创融合之间的双赢之路。